|
由北京市科协推荐的病毒学家顾方舟获“人民科学家”荣誉称号,来听听顾方舟主席的“科协故事”。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签署主席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17日下午表决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顾方舟、叶培建、吴文俊等人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顾教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1年留学苏联。1955年获苏联医学科学院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科协常委、北京市科协主席、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顾方舟主席与北京科协 作者:田华新(北京市科协退休干部) 
▲1991年11月13日,在市科协四届一次全委会上,顾方舟当选为北京市科协主席并讲话 顾方舟先生1986年9月至1991年任北京市科协第三届副主席。1991年11月至1997年1月任北京市科协第四届主席。他是继茅以升先生、王大珩先生之后的北京市科协第三位主席。1997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北京市科协名誉主席。 在顾方舟担任北京市科协主席期间,通过他的努力和科协、学会同志的共同奋斗,市科协工作取得重要成绩和新的进展。 顾主席始终强调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他认为科协委员会要充分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正确认识科协的优势,不断更新观念,坚持改革,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科技社团工作的新思路。他在多次讲话上谈到,中国特色的科协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科协的学术交流和科普工作。这是我国科技团体的传统,也是一大特色。二是参政议政。科协在政协有自己的席位。科协要通过政协以及其他渠道,以多种方式向党和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反映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呼声。三是要围绕党和政府的重点工作,开展活动。 1991年11月13日,顾方舟当选市科协主席。他主持的市科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会议上,有常委提出每季度由市科协组织一次座谈会,请市领导与专家学者面对面对首都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提出建议。顾方舟主席当即表示支持,并代表市科协当面向市领导提出这个建议。14日在市科协四大闭幕式上,市长代表市委、市政府同意由市科协组织建立市长听取科技专家意见的“季谈会”制度。五年间,市科协在开展学术研讨的基础上,认真选题,组织科学技术专家“季谈会”12次,71位中央单位专家、53位北京市专家、12位市领导先后出席。专家提出具体建议300余条,内容涉及提高京郊农业的质量和效益、首都发展战略研究、修订北京城市总体发展规划方案、解决首都电力供应不足途径、改善城市环境、缓解水资源短缺、防灾减灾对策、科技扶贫、加快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发展建设、加强科学普及和实施首都信息化工程等方面。现在“季谈会”已成为市科协精品活动之一。 1992年初,市科协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提出要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上有所突破,在科协系统实施“金桥计划”。4月11日主席办公会议上通过“实施金桥计划纲要”。1993年根据中国科协的建议,“金桥计划”改名为“金桥工程”。中国科协发文向全系统介绍北京市的基本做法和经验,向全国推广。1993年5月4日,主席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市科协金桥工程奖励办法。1994年1月12日,中国科协在全国金桥工程汇报会上,专请北京市副市长胡昭广同志到中南海,向国务委员宋健同志汇报北京市开展“金桥工程”的情况。五年间,上报市科协的“金桥工程”项目1437项,其中受市科协奖励的451项“金桥工程”项目增加经济效益20亿元以上。北京作物学会组织实施推广冬小麦新品种京冬8号金桥工程项目,累计推广200万亩,使农民增收1亿元,获全国“金桥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北京燕化公司大修厂科协搭桥的燕化乙烯改扩建化工一厂火炬气回收装置不但每年回收火炬气取得1000万元的经济效益,还减少了环境污染,获全国“金桥工程”优秀项目二等奖。现在“金桥工程”已成为市科协又一精品活动。 顾主席站在全球化的高度看待学术问题。他说,学会的功能不仅仅是促进学科发展问题。繁荣学术交流是首位的,非常重要的。但是,学术里头有政治。现在讨论的环境、气候、生物多样性、生物工程、基因操作、水资源等许多问题看起来是科学问题,实际上是当代全球性的问题,涉及国家的经济、社会利益,涉及国家的安全。他主张,科协和学会要扩大开放,要多参加国际学术团体的会议,并千方百计在国内组织高水平的国际会议。1992年10月12—14日顾主席参与筹备并主持了在北京召开的“人类基因治疗国际会议”,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亚洲举办。18位外宾,142位国内代表出席,大会宣读论文32篇,就遗传病的基因治疗和恶性肿瘤的基因治疗进行了交流。这五年间,市科协多渠道开展同海外的民间科技交流,接待国际和港澳台来访科技团组934个,接待访问学者5500人次,派科技人员出国、出境访问1799人次。1994年市科协组织首次北京市赴台湾省科技团,打开了北京市和台湾省民间科技交流的渠道。 顾主席常说,北京市科协身在北京,要为首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科协要以学术交流活动为基础,以首都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学术活动和决策论证、献计献策相结合,既活跃学术气氛,又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第八届北京市政协决定增设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界。1992年9月市科协主席办公会讨论政协科协界委员的推荐提名的原则。顾主席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与北京市政协的科协界委员一起积极参政议政。先后提出了“关于北京地区综合减灾对策建议案”“关于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的若干问题与建议”“关于京郊基层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状况的考察报告”等。按照全委会的决定,市科协围绕贯彻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精神,举办“2010年的北京”战略发展学术研讨会,56个学会进行研讨,提出123篇建议。 顾主席关心京郊农村的发展,关心基层农村科技人员的工作与生活,注重发挥科协在科技扶贫中的作用。1994年顾主席和驻会副主席率领24个学会和厂矿科协的百余位专家,先后18次到昌平区老峪沟、房山区蒲洼乡和密云太师屯镇马场村等10个贫困乡村调研,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顾主席认为科普工作是科协和学会的主要社会职能,科协要面向基层和青少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1995年初,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加强全国科普工作,市科协在顾主席领导下向北京市政府提出根据人口数量设置科普经费和设立每年一次科技周的建议,两项建议均被市政府批准实施。1995年5月,北京市首次举办北京科技周。科技周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主题,组织青年学术年会、新技术新成果录像片巡展、送医下乡、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实验室开放和青少年科技博览会等科技活动2000余项,参加人数达20多万人次。1996年顾主席参加了以“科学·文明·健康”为主题的第二届北京科技周开幕式,第二届北京科技周活动参与人数达到261万人次。“每年5月举办北京科技周活动”已正式写入1998年11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顾主席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格外关系医科社会团体的发展。1984年他和几位教授凑了几万元,筹建并创办了中国免疫学会,与吉林省卫生厅合办学术刊物,为学术交流打开了渠道。他长期担任中国免疫学会和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在他的关怀下,1994年4月成立了北京免疫学会。北京生理科学会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合办的《基础医学与临床》(原名《生理科学》)创刊于1981年10月,在医学界有较大影响。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该刊一度因为经费问题难以为继,顾主席千方百计为该期刊筹措资金,使刊物越办越好,受到医务工作者的喜爱。2003年SARS肆虐,顾主席多次参加防治“非典”的专家研讨会。他撰写的《应对SARS的几点建议》,从加强对抗击“非典”一线人员的保护研究;集中财力选准SARS研究课题的主攻方向;对“非典”尸体从流行病学、病毒学和病理学方面进行研究;抓紧对病历资料的收集整理;通过媒体宣传,使市民树立战胜SARS的信心和提高农民自我防范意识等六个方面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提出建议。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相扶持”。顾主席大力提倡把扶持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作科协的社会功能。他多次担任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的评委会主任,通过举荐和奖励人才,使青年科技工作者脱颖而出。1995年市科协召开首届北京青年学术年会,青年科技人员贺福初的学术论文荣获一等奖,并成为第一位学术论文宣讲人。顾主席出席会议并与青年科学家亲切座谈。2001年,39岁的贺福初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顾主席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对老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关心,他担任中国老科协的副会长和北京老科技工作者总会的会长,主持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老科技工作者作用的调研报告》。北京老科技工作者总会和所属的80个分会,积极组织离退休老科技工作者参加科技服务、社区科普、科学健身、医疗保健和文化联谊等活动,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养。顾会长关心老同志的健康,多次提醒要注意老年痴呆的防治。 顾主席关心市科协的基地建设,在他的关心下,北京市科技进修学院大兴校舍和北京市科协南区办公楼先后投入使用,北京科技活动中心主体完工,改善了科协开展科技活动和培训工作的条件。 顾主席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善于调查研究,讲究政策策略,具有领导素质和学者风范。他对党的改革开放路线表示拥护,对共产主义事业坚定执着,对科学事业赤诚热爱,对科协事业有深厚感情,对北京市科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追忆顾方舟先生 这位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的医学家,在医学领域的贡献是多面的。顾方舟的事业及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后人攀登医学科学的道路上,在建设健康中国的征程中,必将长久地发挥作用。 顾方舟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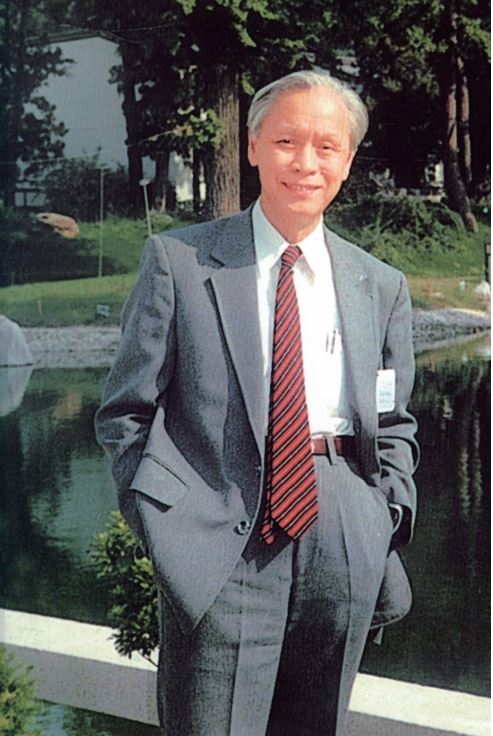
顾方舟,浙江宁波人,病毒学家、教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1955年于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医学副博士学位。原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中国科协常委、北京科协主席、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免疫学会名誉理事长。2019年1月2日,顾方舟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顾方舟研究脊髓灰质炎的预防及控制42年,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1958年,他在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上世纪60年代初,他研制成功液体和糖丸两种活疫苗,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同时提出采用活疫苗技术消灭“脊灰”的建议及适合于我国地域条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
顾方舟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一可怕的儿童急性病毒传染病的战斗中,是我国组织培养口服活疫苗开拓者之一,为我国消灭“脊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埋下学医的种子 1926年,顾方舟在宁波出生。然而,与宁波轰轰烈烈建设场面不同的是,顾方舟的童年生活颇为不幸。他的父亲顾国光,在他4岁时不幸去世。为了养家糊口,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辞去教师职业,只身赴杭州学习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留下年幼的顾方舟交由外婆照顾。 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是孤独、痛苦的。有一次,学校要排演一场话剧,顾方舟非常兴奋地举手报名。但是那么多角色中,老师偏偏让顾方舟演乞丐。同学们都笑话他:笑话他没有爸爸,笑话他家里穷,就应该演乞丐……为了不让外婆伤心,懂事的他只好装作很喜欢演乞丐的样子,还让外婆把哥哥的旧袍子改成乞丐装。 1934年,周瑶琴于杭州广济助产职业学校毕业,带着顾方舟北上天津,在英租界挂牌开业,成为职业助产士。租界里的日子很艰难。地痞滋事、流氓敲诈,警察还借保护之名行勒索之实。一次警察来勒索,恰巧被顾方舟看见。警察走后,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周瑶琴叹了口气,摸着他的头说:“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 在这个国无国格、民如丧家土狗的年代,哪有职业能真的扬眉吐气?但在十多岁的顾方舟听来,“不用求别人”这句话,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从记事起,顾方舟的世界充满同学的嘲笑、老师的欺负、洋人的欺侮、警察的压榨,而以后可以不用求人,不用在乎这些人的脸色,想到这里就欣喜不禁。他的心中悄悄种下了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当医生! 家国间架起的桥梁 1937年7月29日,日本开始攻打侵占天津,一时间尸骸纵横,满眼皆是残垣断壁,数十万百姓无家可归,天津沦为一座人间地狱。顾方舟一家在英租界里,这里是汹涌大海中的一片孤岛,享受着孤独的和平,品尝着亡国奴的滋味。 顾方舟的初中念的是昌黎汇文中学,不在英租界内。每天,顾方舟都要拿着通行证出租界去上学,放学后再拿着通行证进租界。除了以前的课程外,顾方舟和同学们还要被迫学习日语。那些封面上写着方正汉字的教科书,打开全是日语。要是日语学不好、背不出,日本人就会拿着宽宽的木板,叫班长打手掌。班长如果不打或者打得不狠,日本老师就亲自上阵,拿着板子打班长,直到把手打肿了才算完。 每天太阳升起时,顾方舟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日本人凶残的目光,是难以名状的屈辱。每每这时,立志学成报国的念头就在顾方舟的心中燃烧。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在这里,他遇到了严镜清先生。严镜清先生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很陌生:厕所沿街沿河而建,粪便尿溺时常满溢;河水拥有饮用、洗衣、除垢、排污等多重用途;水井与厕所比肩而设,平时村落就垃圾遍地、臭气熏天……卫生环境的恶劣直接导致疾病的流行,死亡率之高令人咋舌。严先生常常讲着讲着,眼眶就红了,顾方舟也忍不住地潸然泪下。 一次,班里一个女生随严老师去河北,考察矿工的劳动卫生状况。回校后她嚎啕大哭,边哭边讲矿上的惨状:矿工毫无保障,穿着麻袋,鞋破露趾,夜枕砖头,日不见天,有时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她边说边哭,周围同学也是闻之落泪。她不知道,她的这番话对一旁的顾方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要做一个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拥抱健康!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自己已进入中国最高学府,又怎能只想着自己呢?顾方舟似乎一日之间长大了,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1947年10月,当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已是党员的顾方舟弟弟找到顾方舟时,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张硕文同志介绍下,顾方舟郑重地在党旗下宣誓,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以身试药 大学毕业后,顾方舟践行了自己求学时的理想,来到了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工作。朝鲜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被派往战场,治疗患了痢疾的战士。1951年,在战场后方的顾方舟被召回大连,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 顾方舟的导师是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夫科维奇教授。1955年夏天,顾方舟以优异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1957年,顾方舟带领了一个研究小组来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在国内的暴发发生于1955年,江苏南通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死亡,随后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全国闻之恐慌。 1957年,顾方舟调查了国内几个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等十二处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并成功定型,发表了《上海市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分离与定型》。这项研究,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并用病原学和血清学的方法证明了I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以此研究为标志,顾方舟打响了攻克脊灰的第一战。 1959年3月,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人到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 当时,美国和苏联均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疫苗分为活疫苗和死疫苗两种。经过几周的研究,死疫苗逐渐揭开了神秘面纱,他失望地发现,美国Salk研究的死疫苗虽有效果,但控制脊灰流行不尽如人意,只能防止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不发病,不能阻止脊灰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此外顾方舟还发现,美国病毒学家Sabin还发明了活疫苗,但始终无法进行安全性试验。 顾方舟意识到,这是关于疫苗生产的技术路线的问题: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他判断,根据我国国情,只能走活疫苗路线。他立刻向国内写信汇报在苏联的考察情况,并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我国不能走死疫苗路线,要走活疫苗路线。 不久,卫生部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协商,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了组长,进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经过一番波折通过动物实验后,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三期。Ⅰ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有无副作用,只需少数人受试。Sabin教授正是困在了这一步,难以前进。 这是一个自强、忍耐、奉献的年代。几乎是毫不犹豫的,顾方舟和同事们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去后,顾方舟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 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因为他面临着一个他一直担忧的问题—成人本身大多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呢?又有谁愿意把孩子留给顾方舟做试验呢? 望着已经进展至此的科研,顾方舟咬了咬牙,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这些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人,用一种看似残酷的执着,表达着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的爱。这是科学史上值得记载的壮举,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辉煌史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测试期慢慢过去了。面对着孩子们一张张依然灿烂的笑脸,顾方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相拥庆祝:疫苗是安全的!努力没白费,疫苗是安全的! Ⅱ期临床试验是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1960年,在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研究方案后,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 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最终大考:流行病学检测。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一下子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了试验。近一年的密切监测表明,各市脊灰发病率产生了明显的改观。未服疫苗组发病率比服疫苗组高7.2~20倍。三期临床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顾方舟研究的疫苗可以投入生产、给全国儿童服用了。 打响脊灰歼灭战 早在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1959年1月,将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1961年10月,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顾方舟向总理汇报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生产状况 生产基地的建设面临着设计资料少、交通运输困难、物资紧缺、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的困难。顾方舟后来回忆时说:“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儿,就说:‘行!虽然有困难,但是能够克服的,一定努力干!’那时候我们住都没地方住,搭起炉灶来就那么干,吃也吃不饱,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九个月后,有19幢楼房、面积达13700平方米的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 1960年的春天,周总理去缅甸访问的途中,路过昆明。在云南省长刘明辉、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的陪同下,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顾方舟对正在视察疫苗基地的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消灭掉脊髓灰质炎!” 周总理听了,直起了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 “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道:“我们有信心!” 周总理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也被总理的情绪带动起来,他紧张的心放松下来,说道:“不会呀!这个病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病呀!”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十一个城市推广开来。经过广泛的调研,顾方舟等人很快掌握了各地疫苗使用情况,捷报像插上了翅膀纷飞而来,传到了顾方舟的手中: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着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敏锐地意识到,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这样就给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疫苗是液体的,装在试剂瓶中运输起来很不方便。此外,服用时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还不愿意吃。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问世了。除了好吃外,糖丸疫苗也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推广。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这些发明,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糖丸疫苗, 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阶梯形下降。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着脊髓灰质炎的研究。1981年起,顾方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1982年,顾方舟研制成功“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 “脊灰”单抗。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位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工作奉献了一生的老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赞美。 
▲2002年在何梁何利基金2001年度颁奖大会上,顾方舟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甄永苏院士同获科学技术进步奖 (本文摘自《北京科协》,内容综合光明日报、中国科学报等,部分内容来自学习强国、新京报,由北京科技报全媒体中心综合编辑)
|

